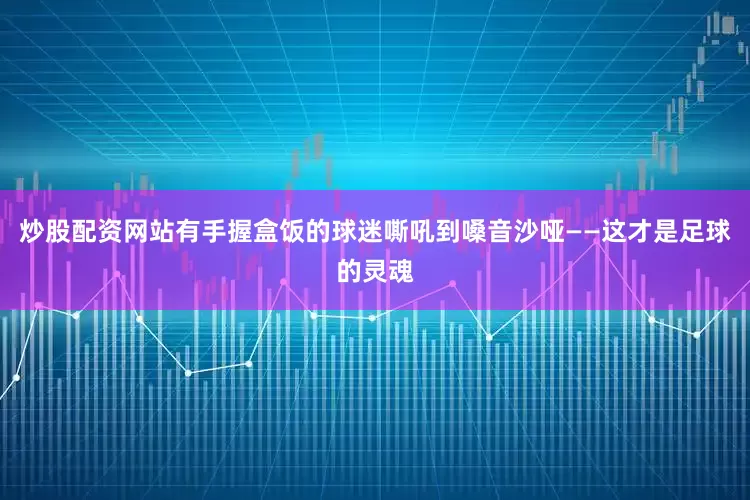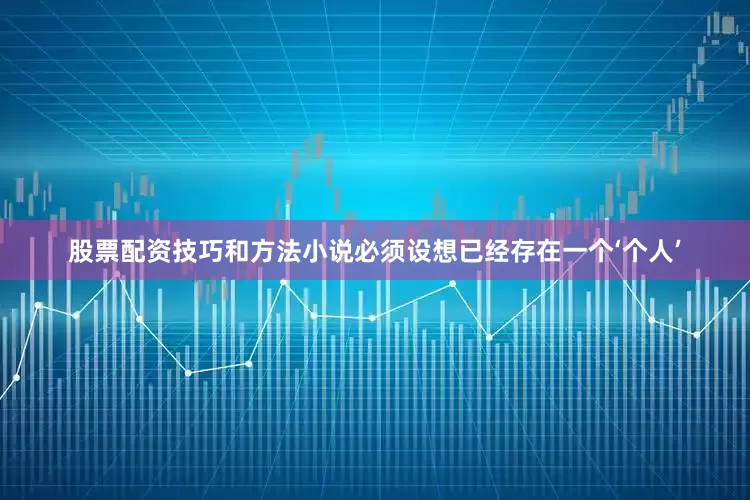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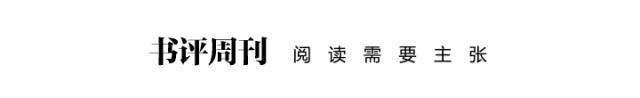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在AI迅速发展的当下,我们热切地讨论着写作的限度与独特性。
小说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仍然被认为其中保存着人类的“灵光”。它可能被模仿,却难以创造出同样的光晕。即使在视觉信息爆炸的当下,小说仍然构成了基础的文学脚本。
在细腻、感性、富有创造力的标签之下,小说对现代世界还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力。伴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催生了一批“能够阅读的公众”,自那时开始至今,小说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最近出版的《小说如何思考》一书中,学者阿姆斯特朗分析了现代小说与现代个体的诞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她指出,要不是“小说”把个人主义这一哲学概念转化为叙事形式,它是否会在西方快速且彻底地形成和传播将成为一个问题。小说如何影响了现代个体概念的诞生?它们之间又是如何彼此限制的?

撰文|重木

现代小说的兴起
在美国著名文学史家伊恩·瓦特(Ian Watt)看来,小说(novel)是一种诞生自18世纪英国的新兴且特殊的文学类型,它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神话、史诗与悲剧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在其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作《小说的兴起》中,瓦特通过研究三位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笛福、理查逊与菲尔丁——指出“小说”这一文类得以诞生的内部与外部原因。前者主要涉及对传统“现实主义”概念的重新诠释与理解,后者则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受教育阶层的出现息息相关。
在康德的《何为启蒙?》一文中,我们能清晰看到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围绕着如何运用人的理性而建构起的现代教育体系,催生了一批“能够阅读的公众”,而这些能阅读者所阅读的书籍不仅有洛克、休谟与卢梭这些启蒙哲学家,还有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诞生的新兴文类,即小说。
就如瓦特所指出的,读者群的产生及其需求使得“小说”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受众,而恰恰也是通过这一互动,使得18世纪的启蒙思想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与塑造着现代个体、社会与国家对自身的想象与形象。而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的小说研究工作也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中展开。
《小说的兴起》
作者: [美] 伊恩·瓦特
译者: 李树春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10月
在阿姆斯特朗出版于1987年并使其一鸣惊人的专著《欲望与家庭小说:小说的政治史》中,她一方面延续着瓦特对于小说之诞生及其发展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她通过关注家庭小说以及女性这一特定对象,而超越了瓦特的研究范式与范围。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瓦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8世纪的主流且经典的男性作家及其作品,因此对于作为“支流”的通俗、商业或大众小说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而阿姆斯特朗在其代表作中关注的恰恰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的正典文学史建构中都地位可疑的家庭小说。
在经典的小说史论述中,家庭小说往往被置于通俗领域,且因其读者群往往被预设为家庭女性,而使它难登大雅之堂。但在阿姆斯特朗看来,恰恰是在这类围绕着家庭生活所展开的小说中,隐藏着18世纪启蒙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诞生的历史秘密,因此发掘其中被遮蔽的政治内涵就成为阿姆斯特朗小说研究中最重要且一以贯之的主题。
除此之外,由于阿姆斯特朗的成长与思想诞生自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此我们能在她的研究中看到其时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在《欲望与家庭小说》中,“家中天使”成为破解家庭小说之政治内涵的主要形象,即在这些围绕着“家庭-女性”而建构起的虚构作品中,对于女性及其所呵护的家庭生活与形式的孜孜不倦的关注背后涉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论、道德哲学以及政治斗争,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向传统的旧贵族体制展开批判,从他们的道德观念、政治与社会结构到经济模式,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批判,而其切入口便是区别于传统旧贵族式大家庭的“核心家庭”。
现代个体的诞生
在《欲望与家庭小说》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阿姆斯特朗的研究主题以及她所关注的问题,即现代小说与现代个体、家庭和社会形式的建构是同步且不断共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恰恰是通过“小说”这一新兴文类,使得诞生自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模式获得了快速传播、巩固与再生产的机会。而这些主题我们在阿姆斯特朗出版于2005年的《小说如何思考》中会再一次看到。区别于前作围绕着家庭小说中隐藏的政治意涵所展开的讨论,在《小说如何思考》中,阿姆斯特朗所关注的问题则是现代启蒙思想——甚至是整个现代性——中最核心的问题,即现代个体性。本书的副标题为“个人主义的限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现代“小说的历史和现代主体的历史实际上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则同时指出,在被给予了厚望的小说中所塑造和想象的现代“主体/个体”自始至终都是有限且存在隐患的,即它所依赖的自我建构的模式最终在现代个体性内部留下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而正是这一遗留的问题可能会摧毁现代个体性的自我想象与塑造。
《欲望与家庭小说》
作者: [美] 南希·阿姆斯特朗
译者: 顾路昱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在《欲望与家庭小说》中,阿姆斯特朗就已经指出,家庭小说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写“家中天使”,实则关注的是现代个体性问题,即“女性”形象成为构建现代——或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所渴望与想象的——个体/主体的重要模板。我们会发现,那些被安置在家庭这一特定现代空间中的女性角色逐渐从一种由外部设定的模式转向了对其内在道德、品质与情感的强调。由此开始,一个完美的“家中天使”所注重的不再是她的阶级和社会地位,而是其对于特定美德的遵守与实践。在《小说如何思考》中,阿姆斯特朗通过讨论理查逊的两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诠释了现代小说中所塑造与想象的现代主体形象,即“个人”。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理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核心教义,阿姆斯特朗对其概括如下:
……现代主体的形成依靠从外部世界获取感觉,并首先用这种感觉材料构成观念,然后形成了判断力和道德感,从而赋予主体一种自我封闭、内在一致的身份认同。
对于现代主体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从外部世界获取的感觉材料“构成”观念,康德的理性依赖于先天范畴,但小说却另辟蹊径,它依靠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故事情节与主人公的互动展开,即恰恰是作为“外部”的风景、情节与他人的出现,使得现代小说中的角色获得了一种看似自我封闭且具有深度的“内部”。而这一“内部”也正是阿姆斯特朗所谓的“个人”。“为了生产一个‘个人’,小说必须设想已经存在一个‘个人’,这一个人不仅是叙事主体和写作源泉,也是叙事客体和写作指涉的对象。”而这一“个人”的特殊性正在于其自我封闭与内在一致,它虽然依旧依赖于“外部”的存在(为其设定界限),但如今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我意识以及他对于特定道德伦理与情感模式的实践。后者不是前者的规定,而是它的产物。
因此,就如阿姆斯特朗所指出的,“小说将一种欲望具象化,这种欲望让身体同旧社会为个人自我实现选择设下的限制之间发生冲突,让身体从社会等级的标识转化为独特主体性的容器。”曾经被外部等级制度所规定和标记的身体,如今成为一种独特主体性的外化形象,“个人”由此诞生。
因此,我们在18世纪的小说中常常看到一类典型的形象,即“不合时宜者”(misfit)。他/她们对于自身所处的位置、所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和遵守的道德都充满了一种格格不入感,由此导致其与社会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而为了能够解决这一岌岌可危的不安感,18世纪的小说开始为“传统赋予构成18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属性增添了新的特质”,而这一修辞学附加物(rhetorical additive)的目的则是为了将“主人公驱逐出特定位置,将他/她抛进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场域”,而也恰恰是在这一“可能性的场域”中,主人公将得以超越不断束缚他的外部规范,并通过自身的实践来重塑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道德与情感领域。这一在传统等级制社会中被禁止的流动性,让这些主人公成为一种例外,而也正是“这一点令这些主人公个性化了,与此同时又让他们成为一般人的典范。”
《小说如何思考》
作者: [美] 南希·阿姆斯特朗
译者 : 罗萌
版本: 大方| 中信出版社 2025年9月
对于这些“不合时宜者”而言,正是一种来自个体内部的不满足感使得他与自身被规定的社会地位之间产生了距离,而为了弥补这一沟壑,一股被洛克称作“欲望”的动力就会产生,在这股动力的催动下,不合时宜者一方面逐渐偏离与超越了自身出生所属的阶层,另一方面他最终将会发现真正的道德价值并不来自于外部的社会规范与教条,而是存在于个体之内,而不合时宜者在其欲望下的不断流动恰恰是为了发现那些早已经存在于自身内部的“纯真”价值。
在18世纪的小说中所展现出的正是这一不断“成为”与“执行”的过程,即现代主体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存在状态或一个位置,而是一种通过与外部不断地偏离与对抗而逐渐创造出的新位置,它“与其欲望和能力相称”。最终,这些不合时宜者不仅未被社会所抛弃或禁止,反而成了新的道德典范。在这一时期,“不合时宜者”与坏主体被赋予了强烈的活力,它所暴露出的恰恰是资产阶级对于旧贵族制度的批判与攻击——不是个人错了,而是封建社会出了问题,因此如何依赖个体的理性与道德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的平等的社会,成了现代个人自我想象与塑造中所获得与创造出的最大合法性动力。
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现代主体性建构本身内含着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在阿姆斯特朗看来,它主要表现在现代世俗国家的教育制度所强调的主体性自由——“个人”即意味着“一个主动权的中心,能发起行动并对其负责”——与社会服从之间。尤其伴随着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使得传统的“不合时宜者”式的积极主体以及其对于社会规范的威胁开始成为新的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便成了19世纪小说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个体性与共同体的冲突
在阿姆斯特朗看来,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小说主要被一对辩证关系所塑造,即主体性与服从。由此现代个人也不得不要在这两种存在状态之间进行协商,而最终的结果显然区别于18世纪的模式,它主要是“通过拒绝安于一个不能提供满足感的位置,18世纪的主体要求社会秩序放松边界,把一些被体面社会排除在外的元素包容进来”,但如今,伴随着对于“自由”的重新诠释,在自由主体性与更高权威的服从之间,小说“为了社会稳定极不情愿地放弃个人主义”,而家庭情感和社会责任成为这个世纪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19世纪的主体不得不经历一场内部革命(internal revolution),即将在18世纪的小说中那些被赋予了积极意义的“社会性野心重新导向社会接受的目标”,而这一新的主体也开始“使自己适应一个较其主体性而言更为受限的位置,构成了隔绝的内心世界,在社会层面上仅得到局部表达。”
《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者: 吴叡人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区别于曾经独异的“不合时宜者”形象,在19世纪的小说中,曾经为其提供对抗社会的过度个人主义,一方面开始被约束与节制,由此形成了复杂的自我管理与治理术;另一方面则需要把它引导到一个更大的目标上,即通过自我节制而塑造出的同质化主体最终将构成一个“一致性的整体”,而它恰恰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基本单位。如今,“自由主体性是关乎公民资格并和它一起发展的东西,而非起源于其外部且先在于它”,因此自由主体性开始被置于社会之内,而非如18世纪启蒙思想所理解的外在于社会,从而为一个“整体”的塑造提供基础的框架。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他便意识到现代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自我想象与塑造的功能,或如阿姆斯特朗所指出的,“那些住在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人开始根据是否遵循以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标的自我控制形式,来斟酌他们的同胞在多大程度上算得上一个英国人。”
个体性与共同体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就如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对于过度的个人主义的批判:一旦超过了“个人”的界限,个体就会成为怪物,从而失去他在人类共同体内的成员资格。至此,曾经在18世纪风靡一时的“不合时宜者”——他们作为典范、作为新世界的英雄——逐渐退场,表达型个人主义也随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自我约束与节制,它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现代公民的资格与责任,从而创造出一个十分有限的共同体形象。
而在19世纪这一有限的共同体中,相比于男性,女性不得不遭遇二次规训。在维多利亚时期,伴随着资产阶级家庭秩序的制度化而塑造出的男女两性形象与气质决定了任何过度行为都会遭到惩罚。对于19世纪的女性而言,她们被鼓励以一种区别于传统——“通过过度行为让自己有资格讲出如何成为个人的故事”——的形式存在,即如简·爱那样“把过度特质内化”,而非张扬。在阿姆斯特朗看来,如摩尔或伊丽莎白·班内特这些18世纪的女主人公们“拓展了自我表达的限度”,但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主人公们则收缩了这些界限,从而把“个人主义能量转化为自我管理和控制的形式。”在对这一转变原因的讨论中,阿姆斯特朗指出它实则是我们自身所处环境的投射产物。
《书店》剧照。
归根到底,男性气质的不稳定与个人主义的内在矛盾息息相关,即它们都以一种排斥性的包含模式构建自身,由此导致它们难以在幻觉(即自身的独立与完整性)与事实(即依赖于其排斥又包含的“外部”)之间达成平衡。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所塑造出的男女两性气质及其关系的困境或许也就是现代个人主义的限度,即它不得不以一种排斥性的包含模式进行自我想象和塑造。
例如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利用性别——性差异的幻象——来维持包容性的幻象”,而一旦小说将男性气质中不能同化的特征重塑为女性,“那么它就可以在不牺牲‘普遍性的人’的幻想、也不违背‘某些人类特质明显超出西方文化的限度、因此够不上人性’这一信念的前提下,着手驱逐这些特征”。只是这些驱逐总是难以穷尽且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为被压抑的东西自始至终都存在于这一结构之中,并在移置的作用下不断地以某种鬼魅的形象折返,这也就是哥特小说的焦点所在。
小说与个人主义的传播
阿姆斯特朗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小说关注的是“如何利用个人能量服务社会目标”,而另一类小说——通俗且大众的罗曼司与哥特类型——则探索了另一种备选的可能性,在这些虚构作品看来,“我们不过是欲望的强化点(point of intensification),这些欲望通过我们循环流动,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盲目失察的人类群体”。
为此小说开始——在阿姆斯特朗看来,是“不得不”——去想象那些非自然和异常的事物,以此来维系规范性主体,且让读者渴望化身这样的主体,因此它必须把某些“个人主义的过度行为”判定为不可想象之物。在罗曼司与哥特小说中,现实主义原则被推翻,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现实主义就是个人主义本身的限度”,然而作为“另一种备选的可能性”,在这些充满想象和破坏性的创造力中,它们又把“逃离个人主义的限制的快感与人性的丧失等同起来”,因此也就导致我们最终不得不再次去捍卫个人主义……
为此,这些突破了现实主义原则的小说从另一个方向与那些“赋予现代个人以形式并持续保卫它、更新它的文类达成了一致”。
《书店》剧照。
这或许既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个人主义的限度,也是小说的限度,尤其当它以排斥/包含模式来想象与塑造现代主体性时。因此,阿姆斯特朗建议我们,如果想要制定出更恰当的“人类”观念,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以肯定性而非否定性的措辞来阐明我们所缺乏的东西:我们因始终且必然无法达到文化规范的标准——这种文化规范为现代个人所蕴含,并由核心家庭提供再生产——而获得共同性”。
作为“现代(性)”中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小说不断地以自己特殊的形式思考着现代个体的存在与它的在世生活。或许就如阿姆斯特朗所认为的,要不是这一新兴的“小说”把个人主义这一哲学概念转化为叙事形式,它是否可能在西方快速且彻底地形成和传播将成为一个问题。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重木;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传金所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